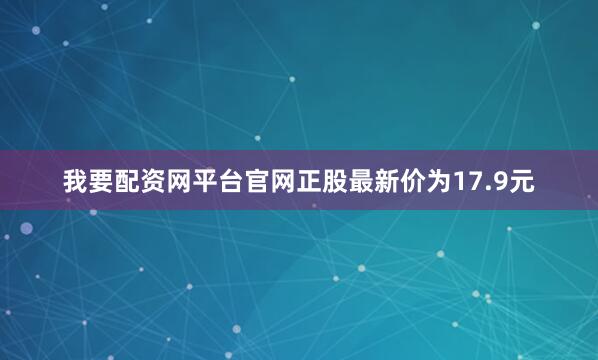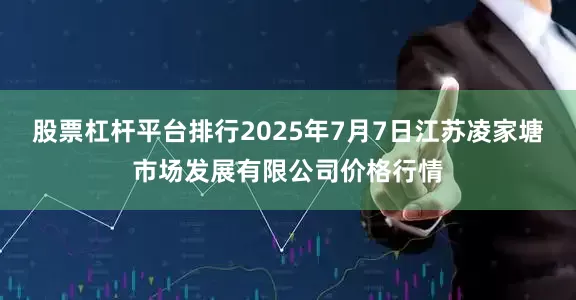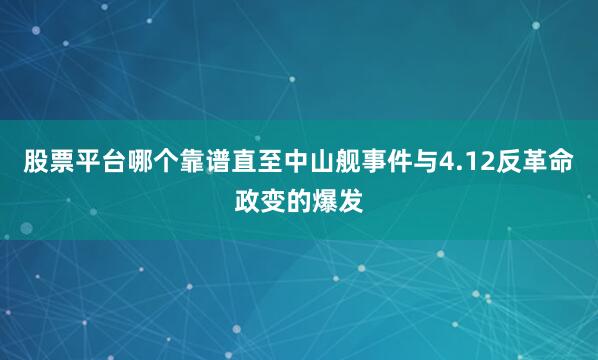
1923年,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率领一支代表团前往俄国进行访问。在此之前,蒋介石曾多次向孙中山提出申请,而在此期间,他亦已做了周详的准备。即便是在航船上,他亦不懈地学习俄语,心中满怀期待,终于能够踏足向往已久的“共产主义的摇篮”。然而,正是这从九月到十一月的三个月访问,使得蒋介石对苏联及共产党的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1951年6月5日,在四川省合川县南津乡,当地农民点燃了地主手中的土地契约书,以此欢庆土地改革事业的辉煌胜利。
蒋介石的形象复杂多样:他是革命家,亦或是反革命;他既是坚守传统的保守派,也是善于变通的机会主义者;他既是一个注重自身形象的政治家,又是一位在乱世中崭露头角的军人。他身上集合了固执与灵活、温情与刚毅、坚毅与软弱等多重性格。尽管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分析,试图找出这些性格的轻重主次,但不同的视角和关注点可能导致不同的结论。
在我们传统的认知中,蒋介石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对立场似乎自始至终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随着近年来蒋介石私人日记的逐步解密,以及国内外历史学家的不懈研究,这一观点正逐渐受到新的审视与探讨。事实上,蒋介石在年轻时曾深受共产主义信仰的影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那么,他究竟是在何时偏离了这一立场,走上了反对共产主义和人民的道路?他的一生中,对苏联及共产党的看法经历了怎样的转变?本文将深入挖掘蒋介石的公开演说、演讲文稿,以及他的著作,并辅以近年来解密披露的蒋介石私人日记,综合分析其言行,以探究相关议题。

蒋介石
早年信仰马克思学说
蒋介石,与众多青年同代,深受辛亥革命及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其思想亦被马克思主义的潮流所浸润。他不仅阅读了如《新青年》这等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期刊,亦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著作。在其1923年的日记中,多次提及“阅读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研读《马克思学说概要》”等内容。他不仅对马克思的学说深入研究,更是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在1923年10月18日苏俄访问期间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研读马克思学说。午后,再次翻阅。久久沉浸于其中,难以放下卷轴。”“研读《列宁全集》,其中论述了权力与联合民众在革命中的必要性,并强调了通过友谊般的感化和训练来团结民众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基于经验的真知灼见。”
蒋介石在早年亦未曾对苏联抱有敌意。当孙中山着手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并携手苏联代表越飞共同发布《孙越宣言》之际,蒋对苏俄评价亦佳。1923年8月5日,蒋介石亲笔撰写了一封题为《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的函件。强调“苏联是我国唯一的盟友,我国革命的兴衰成败,与苏联的关系密不可分。”“时至今日,帝国资本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愈发严重。中俄两国之间主义的紧密联系,其兴衰与否,实则关乎存亡共命运。”
蒋介石在早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深感兴趣,并屡次表达对苏联的亲近与憧憬,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最终走上了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呢?
访问苏联:观感转变
1923年,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团赴俄国进行友好访问。在此之前,蒋介石曾多次向孙中山请缨,并在此期间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即使在船上,他仍不懈地学习俄语,内心充满了激动,因为终于有机会一窥“共产主义的摇篮”。然而,正是在同年9月至11月的三个月间,蒋介石对苏联及共产党的看法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变。
蒋介石在苏联逗留期间,其参观访问主要涵盖以下数个方面:
一,会晤苏联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深入交流他们关于苏联革命历程的宝贵经验,同时探讨苏联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所提供的支持与协助。
二,我们得以参观苏联红军、军事学校及其相关设施,深入了解了苏联红军的组织架构、军事学校的运作机制以及先进的军事装备。
三、我们深入参观了苏联各级苏维埃政府机构的运作。这包括了中央政府各部、会的实地考察,以及对市级和村级苏维埃政府组织的细致调研。我们瞻仰了莫斯科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观摩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的研讨会,并与众多党政高级官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俄国人民,无论地位高低,都显得无比诚实与真挚……这或许正是他们立国之本所在!”在一场有400名红军士兵出席的盛大集会上,蒋介石更是对红军战士们表示敬意,他说:“你们成功击败了国内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势力。”“我们此行正是为了学习,并与你们携手共进。”在游览军队之际,他对苏联的党代表体系及苏军的装备表示出了极高的评价。
尽管苏联在军事和革命组织方面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然而,当蒋介石提议在蒙古库仑……自1921年被红军占领在筹划建设军事基地的过程中,遭遇了俄国人的坚决拒绝。此遭遇让蒋介石心生疑窦,他认为苏联人并非真心实意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其背后可能隐藏着为自身利益考量,尤其对中国边疆地区抱有不正当图谋的企图。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我的俄游感悟便如此记录:“然而,当我与他们探讨中俄间的议题,一旦触及苏联自身的利益时,他们的态度便立刻生变。我访俄之际,正值加拉罕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并前来北京与政府商谈新约之际。在十二年的共同宣言中,越飞亦明确表示,苏俄‘绝无在外蒙古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裂的意图’。然而,在与苏俄的党政负责人讨论外蒙古问题时,我立刻察觉到他们对外蒙古的野心并未消减。这一发现不仅让我深感失望,更让我深刻洞悉了苏联所谓支持中国独立与自由的真正意图。”
更甚者,蒋介石洞悉苏联对孙中山的评价颇低。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演讲中,蒋介石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予以高度颂扬,然而,此举却引发了俄国人士以及留学归来的共产党人的讥笑与抨击。这一经历,令蒋介石在内心深处对共产党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1932年,蒋在苏。
同时,苏联给蒋介石留下了诸多负面印象。在参观彼得格勒等地时,他目睹了城市的萧条景象以及海军士气的低迷。他回忆道:“两年前,克隆斯达军港曾以海军军士为核心,爆发了一场革命,旨在反抗布尔什维克的专制独裁以及战时共产主义的残酷政策。然而,这场革命很快便以失败告终。当我们抵达彼得格勒进行考察时,当地政府和海军官员对此事避而不谈。但从当地军民的精神状态中,我仍能察觉到那段历史的创伤。”而且,随着他在俄国逗留时间的延长,他对该国社会的认识也日益加深。他逐渐得出结论,认为苏俄政府“言而无信”,且存在“少数人种掌握政权,排斥异族”的现象。指斯大林清党等等
归国之际,蒋介石于呈递孙中山的《游俄报告书》中,详述了苏俄存有觊觎边疆之野心,并警示不宜对其过度信赖。然而,孙中山却对此表示异议,认为“未免顾虑过重,实不适宜于现今的革命形势。”
“在参加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我目睹了共产分子倚靠苏联而自抬身价的行为,以及部分党员对共产主义的盲目追随,这使我深感忧虑,因为我们的党未能履行国父所交托的使命。因此,在大会闭幕之后,我坚决辞去了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职务,并将筹备工作交托给廖仲恺,随后我离开了广东,回到了故乡……”

廖仲恺
1924年3月14日,蒋介石致信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函件洋洋洒洒,篇幅不短。将苏俄称为“凯撒帝国主义”。“至于兄长提到中国代表总是遭遇不幸,以张某为例,实在是与事实相去甚远,未免过于牵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国人,而忽视本国人的价值。就像我国派驻俄国的共产党员,只知道指责他人为美奴、英奴和日奴,却不知自己早已沦为一名俄奴。”
无疑,正是这数月的苏俄之旅,彻底颠覆了他对苏联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固有认知,使其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蒋介石对苏维埃制度深表厌恶,对于该政权所推行的各类阶级斗争方式亦感不适。他认为,“在苏联的社会环境或是俄共内部,斗争无论是公开还是隐蔽,均在持续进行。”在他看来,苏联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治制度,作为世界上首个无产阶级政权,竟被定性为“专制与恐怖的机构”,这与我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政治体制,实乃格格不入。若非我亲赴俄罗斯,那国内所构想的景象,终究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在心中,苏联这位“工人阶级的祖国”,在他眼中,其野心远超前任的沙俄,更似一位帝国主义的巨擘。总结我在俄罗斯三个月的考察经历,我内心不禁生发出一种忧虑,那就是若俄共政权未来变得更为稳固,那么帝俄沙皇时代政治野心的复苏或许并非遥不可及。这样的情形,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及国民革命的潜在威胁,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与国民党携手的共产党,在他看来,实则并未真心诚意地支持孙中山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理念。那些共党分子及其同路人,往往以唯物论与阶级斗争的视角,对三民主义进行扭曲解读。在他们眼中,唯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对三民主义进行曲解,方能称之为“革命的思想”。与此同时,他们反将本党党员对三民主义的准确阐释斥为“不革命”或“反革命”。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将宣传部长戴季陶和青年部长邹鲁排挤出党,导致他们愤然离开广东。
他亦将共产党员视为潜伏于国民党内部的巨大威胁,坚信共产党正对国民党实施渗透、分化以及挑拨离间的策略。:“对于当时共产党对我国民党所采取的分化、隔离、制造矛盾等策略,我们看得尤为透彻……他们回国后,便以访俄代表团内部意见不一为幌子,试图掩盖苏俄的真实情况,并发布考察报告书以混淆视听。”、“共产党人起初并未意图全面掌控我党组织。他们的第一步是渗透,第二步则是分化。因此,他们在党内竭力打造所谓的‘左派’、‘右派’和‘中派’等标签,并大肆宣扬‘革命向左转’的口号,同时进行挑拨离间。结果,我党党员在共产党的跨党分子分化与挑拨下,内部矛盾重重,相互排斥,而共产党人则趁机掌握了党的党务和民众运动。就在我党改组成立不到半年的光景,赤色势力便开始嚣张,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深切忧虑。”

黄埔军校
自蒋介石踏足苏俄之地,便对苏联及共产党心生嫌隙,然而,直至中山舰事件与4.12反革命政变的爆发,他尚未公然表达对苏联和共产党的反感。在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他对入伍生发表训话时曾言,无论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均旨在为无产阶级谋求生存而奋斗……我们渴望党派取得成功,主义得以实现,唯有借鉴俄国共产党的做法,方能让所有人明了党员的责任所在。若要实现三民主义,势必要效仿其方法。“在我国,提出设立党代表制度的是我本人。这一制度,正是借鉴了苏俄红军的做法。”
蒋介石万万料想不到,三十年前在保定军校结识的老友段云峰中将的两位公子,竟先后踏入他的亲信机构——侍从室;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出身将门的英才竟纷纷投向了共产党怀抱。《打入蒋介石侍从室》一书记述了段伯宇、段仲宇两兄弟如何凭借他们的特殊地位,制造铁路运输的拥堵和中断,阻碍国民党军队和物资的南移;他们不仅协助策划了国民党伞兵三团的起义,还密谋了蒋介石尤为器重的预备干部总局的起义,展现了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场面……
北伐清党、“五次剿匪”
举世瞩目的中山舰事件,标志着蒋介石发起反革命政变的序幕。鉴于中山舰事件在历史上仍存在诸多未解之谜,且本文旨在探讨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看法,因此,让我们一同回顾蒋介石本人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1925年,孙中山先生仙逝之后,国民党内部逐渐分化为两大阵营。其中,那些已经明确表明反共立场的党员,在北京和上海另行组织集会,他们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而在广州,党的中央负责干部仍能保持团结,并未出现明显的分裂迹象。然而,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本党内部的分化作用愈发积极,他们挑拨离间,制造了左右两派,将胡汉民、戴季陶以及坚持反共立场的本党党员划为“右派”,而将汪兆铭、廖仲恺以及倾向共产党的本党党员划为“左派”,并进一步挑拨胡汉民与汪兆铭之间的信任,导致双方相互猜疑和冲突加剧。八月二十日,廖仲恺不幸遇刺,使得本党中央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动荡之中。蒋介石持续强调,共产党正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分化和离间:“此时,共产党极尽其分化我党的手段,尤其在所谓的对‘右派’的斗争中,对汪兆铭的包围愈发紧密。汪兆铭也终因共产党的煽动而受到影响,在共产派的压力下,以廖案嫌疑为由,被迫以出使俄国的名义离开广东,赴国外。随后,共产党运用以往挑拨胡汉民与汪兆铭关系的惯用伎俩,转而用于挑拨汪兆铭与蒋介石之间,从而在我党内部制造了新的矛盾。”
而中山舰事件在蒋看来,正是当时的共产党员李之龙调动中山舰阴谋暴动所引起的,是苏联和共产党要夺权的阴谋:“三月十八日,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矫令我的坐舰中山号由广州驶回黄埔。他对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奉校长命令,调舰特来守候。”这时我在广州省城,邓来电话问我此事如何,我茫然无所知。随后李之龙亦打电话问我:“中山舰是否仍要来广州迎接?”我很骇异,就问他道:“是谁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回黄埔去的?”他答不出来。其实他驶回黄埔,是要先在黄铺装足煤斤,以备临时远航。到了十九日的晚间,中山舰开回广州,舰上升火,通夜不熄,戒备极严。我知道共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对李之龙等共产党人进行了逮捕。,他们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宅,并没收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枪械。借此机会,他们打击了党内持敌对立场的右派势力。随后,他们向苏联顾问鲍罗廷提交了《整理党务案》,在案中提出了一系列旨在限制共产党活动、巩固国民党党员地位的要求。逐渐开始了“限共”,但蒋介石为了取得苏俄的支持表面上仍维持着“联俄容共”。直到众所周知的四一二清党发生。
1926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庄严誓师,拉开了北伐的序幕。国民政府以此为出发点,确立了以“击溃吴佩孚,联合孙传芳,忽视张作霖”为核心的战略方针,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战火迅速蔓延至湖南,攻占了平江、岳阳等要地。8月31日,大军云集武昌城下。进入9月初,北伐军对武汉三镇发起了猛烈攻势,6日、7日连续攻占汉阳和汉口。10日,武昌也落入北伐军的掌控之中,数月之内,北伐军所向披靡,连克北洋军阀的据点。
尽管苏联顾问与共产党亦参与了北伐,然而蒋介石对这批“异己”势力显然抱持着敌意,他坚信中共是在苏联的指令下发动农村暴动,意图分化革命力量,破坏北伐进程。他在《苏俄在中国》里是这样说的:“十一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作成“中国问题决议案”……要中共党徒利用国民政府的机关,接近农民,实现他所谓“农村纲领”,制造他所谓“农民革命”,其目的就是要从农村暴动中组织武力,建立共党政权。莫斯科为了指挥中共,实行其“彻度的农村政策”,认为鲍罗廷不够激进,再派罗易和谭平山来到中国……中共为了执行莫斯料这一决议……趁着国民革命军的进展,从本党的民众运动中,纠合城市和乡村的游民无产者 (地痞流氓),操控工会与农民协会,煽动武装暴力……旨在分裂我党,并挑拨国民革命军之间的关系,制造各军间的利益冲突,进而乘虚而入,渗透我国民革命军,以此扩张其影响力,增强其控制力。”
“观诸中国各地之俄领事馆,实际上等同于第三国际的支部,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阴谋活动的温床。”

南昌起义
他对共产党当时引发的农民武装起义持强烈反感,将其视作“杀人放火”的行径,以及“制造仇恨”的源头。据其子蒋纬国所述:“我父亲曾言,共产主义的最大缺陷,便在于其缺乏人性。”
他坚信,共产主义革命与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伦理观和民族特性存在本质上的对立。:“以仇恨为动力的革命,与中国民族的性格格格不入。毕竟,若动机源于仇恨,其行动必然趋于残酷与卑劣,且往往以损人利己为目的,这与我国民族性格相去甚远。我国数千年的伦理观念始终秉持利他主义,而非自私自利。因此,我国民族的固有特质是和平、宽容与光明。我们既不愿遭受他人的残酷对待,亦不愿对他人采取残酷手段。”
然而,他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亦持异议,坚信中国社会不宜推行阶级斗争:“我国近代产业尚未充分发展,阶级差异并不显著。若勉强言及阶级,也仅是阶级形态的初步显现。阶级间的对立既不明显,其利益冲突自然微乎其微。既然阶级间的利益冲突不强烈,便无需为某一阶级的利益而颠覆其他阶级。更不用说,为单一阶级的利益而颠覆众多阶级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此,我们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为出发点,消除阶级差异,而非以阶级利益为出发点,从而导致社会的分裂。这一观点基于我国的社会现实,表明共产党的阶级革命并不适宜我国。无论是反帝斗争还是农工解放,我国均不宜采取阶级斗争的策略。”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及其后续的宁汉合流,迫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走上自主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朱德等革命先驱在南昌及各地发动起义,构建革命根据地,并在江西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南京国民政府稳固以及中原大战尘埃落定之后,蒋介石得以腾出精力,着手进行所谓的“剿匪”行动。1930年10月10日,他在南京公开发表《告全国同胞文》,强调“肃清匪共”是当务之急,从而开启了连续的五次“剿匪”战役。
在他眼中,这股小小的共产党势力,其对中国未来的威胁,远甚于盘踞在关外的日本侵略者。他更是将“剿匪的成败”与“国家的存亡”紧密相连。:“众所周知,历史长河中,几乎每个朝代都曾出现过土匪。特别是在新旧交替的动荡时期,即国家从混乱走向治理的关键时刻,土匪的破坏尤为严重。历史上每当出现这种局面,国家的兴衰存亡便往往取决于剿匪的成效。若政府能够成功剿灭匪寇,国家便能恢复安宁与稳定,持续发展;反之,若政府无力剿清匪患,国家将逐渐陷入混乱、贫困,乃至走向衰败乃至灭亡。当前我们所面临的环境,正是如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社会各界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爱国运动,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需安内”的政策,继续其“剿匪”。而对于学生及社会各界的爱国运动,他认为那本是爱国运动,但却受共产党所利用,为共产国际所指使的“人民阵线”作宣传活动,“挑拨地方军与中央军的感情,唆使地方军,在“抗日不剿共”,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之下……孤立国民政府与中央军,让共匪得以生存和发展,重整武装,准备下一次的叛乱进攻;而其所标榜的主张却是“抗日救国”,更显然是企图引起中国抗日全面战争,使共匪在抗战阵营的背后,扩大武装,乘机坐大,达到其颠覆政府,控制中国的目的。”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成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国共二次合作一致抗日。而在蒋看来,张和杨是与共产党勾结已久的:“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不过当时张学良与共党直接的接触,已有半年之久,故共党与张之关系,亦自到了相当的程度,而且首倡此议的杨虎城,其与共党勾结更深。”
西安事变及其后续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迫使蒋介石搁置内战,开启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序幕。尽管蒋介石在表面上接受了中共红军的合法地位,但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实则并未发生根本转变……
启恒配资-股票怎么加10倍杠杆-专业的网上股票配资-靠谱配资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